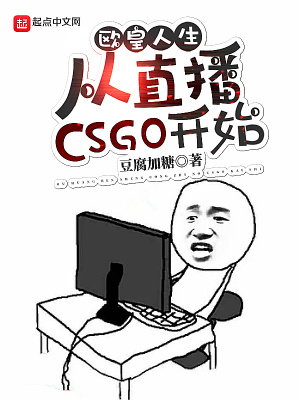中文小说网>小燕尔发电姬全文免费阅读 > 第106章 杀鸡儆猴(第5页)
第106章 杀鸡儆猴(第5页)
她思绪仿佛陷入清晰又浑噩的境地,登上马车时没踩好,险些摔了一跤。
云芹沉默地看着她的背影。
或许她不该提的,对陆停鹤来说,有些东西被贯彻了二十多年,轻易推翻不得。
果子只要有一块甜的地方,有人就愿意吃,便也不顾它背面的霉斑。
否则,她们要靠什么度过漫漫年岁。
忽的,陆蔗手里抢了五妹的球,一路小跑出来,高兴道:“娘亲娘亲,我捡到了!我赢了!”
云芹拿过球,实在好笑,刮刮陆蔗鼻头:“出息,和小狗争什么。”
陆蔗皱起鼻尖,蹭蹭云芹手指:“再来,我就是比五妹厉害!”
五妹:“汪汪汪呜汪!”
……
九月,盛京、淮州来了一沓厚厚的信件。
云芹抱着信,一一分类,陆挚几封,陆蔗几封,她自己几十封。
陆蔗小声问陆挚:“娘亲怎么这么多信?”
陆挚:“习惯就好。”
不过,宝珍的信就占了十多封,她想到什么写什么,乱糟糟的。
每次云芹拆信都有点心惊胆战,毕竟她真塞过一片纯金子,也不怕叫人截胡。
晚上,等陆挚处理好信件往来,云芹却还在看信。
他坐在桌子对面,看她一会儿皱眉,一会儿轻笑,实在是好风光。
想到晚饭后,女儿和自己说的话,他一颗心若羽毛,在胸腔里飘来飘去,唇角也勾了起来。
云芹没察觉,她拆了一封新信,忽的眼眸发亮,和陆挚说:“道雪要来杭州!”
前不久,她在信里和林道雪说了织坊的事,林道雪很感兴趣。
林道雪前两年也打算来杭州看织物,因为事务繁忙,一直走不开。
趁这个机会,她想顺着江水赴苏杭。
信是比她本人早一点到的,云芹看到信的时候,她定是在路上,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抵达杭州。
陆挚低声笑:“就是延雅兄难了。”
云芹:“那你怎笑成这般开心。”
陆挚回过神:“我并非笑延雅兄,咳咳,我只是想到一件事。”
云芹问:“什么事?”
陆挚:“阿蔗跟我说,今天陆停鹤来过。”
云芹:“我原想着读完信就跟你说。”
陆挚又笑了:“你不是和陆停鹤说:‘普天之下姓陆的,我只把陆挚和陆蔗放在心里,其他不放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