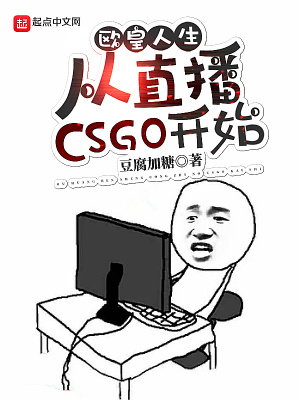中文小说网>杀死因果(双病娇 1v1)-苦渡鸟 > 二百二十三(第2页)
二百二十三(第2页)
一直下就好了。
她把目光收了回来,在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忽然就愣住了。
“什么。。。这是?”
零星几根带子交叉在胸口乃至小腹,几乎只有背部有面料,别说乳头都露在外面,连小穴都是露出的,这不是情趣内衣吗?因果看着他用一只手托住她整个身体,另一只手去打开卧室门,突然挣扎起来,“我不、我不要做了。。。”
还是被他另外一只手又托回来紧紧抱在怀里。
“不做。”他说得轻飘飘,像随时随刻何人何地都能轻易打破。
“那为什么要。。。”
他视线扫过来让因果闭了嘴,笑面虎似的,“防止你再偷偷跑出去。以你的脸面,穿成这样跑出去不如死了,对吧?”
完全被摸透了,因果低下了脑袋。
被放在床上掖好被子,因果感觉自己被放在婴儿床里,也许忠难真应该考虑给她的床加一个护栏,她睡相可差。但原本他就是护栏啊,把她囚在他身体里不得动弹。
只是他没有一起上床,因果忽地抓住他的手问他去哪儿,他沉默的脸在暖光灯下有些渗人,但最终还是摸了摸她的头发,说马上回来,但因果知道他要去哪儿,双手抱上他,脸也贴着他,难以掩饰的慌张表现在脸上是一种很难看的笑。
“你也、你也不能离开。。。”
忠难能拒绝她这别扭的爱意吗?
“小因,”答案是能,“你犯错在先,不要太得寸进尺。”
扒开她章鱼一样的缠绕,她怔怔地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但是小腿都像完全失去神经一样这么软在床里,在空气中完全没有他的存在时她像缺氧一样地把自己缩成一团,整个世界颠来倒去。
也许忠难会立刻发现她去见过令吾了,但至少她是去杀令吾的,他不会太过惩罚于她吧?他如果有那么厉害就该连这种情况都预料到的,不然怎么能是那个令她嫉恨又爱慕的阿难呢?
因果已经分辨不清自己的恐惧来源于何处了,是他也许不会再回来的恐惧?是他发现她见过令吾的恐惧?是她杀死了令吾导致他完美的计划出现纰漏而对她降下怒火的恐惧?是她无法分辨他的爱与恨的恐惧?是未来完全掌握于他手的恐惧?是手脚迟早会被打断被他注射不知名药物的恐惧?
太多恐惧层层迭迭灌进她单薄弱小的身体,尽管她已经被打败过无数次,但死不到来,她手握去死的勇气却扑了一场空,她杀死了母亲,但是杀不死“妈妈”。
“妈妈”就像一块嚼不烂的高粱饴一样黏在她身上。
可她又不能失去“妈妈”。
她觉得自己甚至不像活着了,人了无牵挂尚且能一死了之,她但凡动一个去死的念头都会比死还难受,原本还会纠结他的“爱”到底是什么,现在一想到“爱”只会觉得这是最次的,他要让一切运作下去,就必须控制她,他要让她意识到自己是吃人的怪物,只有他会全身心地接纳她,并且给她他认为最幸福的未来。
在无穷无限的恐惧中她踏进了睡眠。
终究是没能等到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