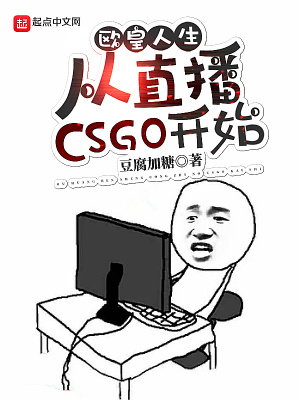中文小说网>攻了那个疯批反派[快穿 > 第47章(第4页)
第47章(第4页)
那确实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路德维希开始庆幸,庆幸当时的他没有丢掉这根手绳。
一开始,手绳上还残留着雄虫身上很淡的信息素气味,那信息素味道很淡,淡到让人无法辨别是何种味道的信息素。
但这是路德维希唯一的触觉,唯一的嗅觉。
唯一能感受的一切。
是洋流的味道,是鲜花的味道。
他站在洋流的风中,站在怪石嶙峋的山岗上,山岗从陆地伸出,面向一片蓝得发梦的大海,遮阴的流簇花在岩石上生长。
路德维希站在迎风的山岗上,浪风吹起他乱糟糟的红发,他在海风与浪声中朝远处看,看到一个模糊的银色轮廓。
所有美好的一切都好似与这轮廓息息相关。
但这一点味道实在太淡了,本来就是从柔软的发丝上摘下来,带不上多少味道,只微末般地残留着,除雄虫的信息素味道外,还有很淡的甜味。
像是糕点的味道。
还有,其他雌虫的气息,总感觉有些熟悉,每当忍不住要去回想更久远的记忆的时候,他就立即叫停,强迫自己不去深想。
是那天约会的那位雌虫吗?
路德维希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心里几乎产生一种暴虐的杀意,所幸这味道本来就没多少,很快就淡去。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他清晰地感受,本来就淡的气味四散着稀释,悄无声息地从他的指间溜走。
路德维希收紧手心,企图去抓住,但无能为力,一切都是徒劳,这最后的感觉也变得无法被察觉。
又陷入长久的黑暗中。
好想睡觉,好想睡觉。
好疼,好疼,好疼。
啊啊啊——
路德维希感到头痛,心脏狂跳不停,一阵慌张的恶心,他死死绷紧脊背,企图去幻想这唯一的存在。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他急切地需要抓住什么——
就在路德维希濒临崩溃时,他听到一道冷淡的声音。
那声音像是洋流携带回来的鲜花,落到他的手心。
“喂,你会做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