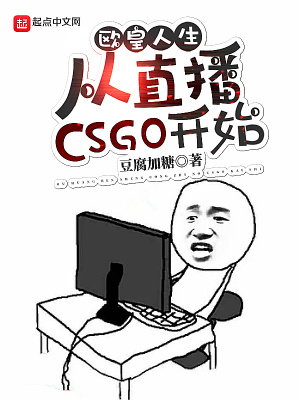中文小说网>黑马人物独胆定位 > 第1章 01 开始的结束(第2页)
第1章 01 开始的结束(第2页)
一哩锦标赛,顾名思义,赛程总共1600米,是中途赛事。而沙田赛马场的草地赛道分为A、B、C三条,长度不等,今天的一哩赛用的是B跑道,全长约1900米,终点线前的直道距离为390米。
前半程在几个呼吸间就过去了,马群在赛道上飞驰,除了一直保持着领跑位置的追月以外,大部分赛马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速度,组成集团跟在后面。
即将进入最后一个弯道,后方的马匹和骑师开始发力冲刺,而此刻,追月和其它赛马的距离已经拉到了七个马身。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注视着赛场上那抹白色的身影。
前几场比赛的不利似乎都在今日消散,追月仿佛一道追不上的闪电,要在自己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创造久违的奇迹,划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但陆茫的心里却升起了某种不详的预感。
他猛地站起身,双眼锁定着追月的身影和奔跑时飞扬的白色鬃毛,浑身都绷紧了,牙关也不知不觉咬住。这一刻他仿佛回到了马背上,纂紧的拳头就像是试图用力握住缰绳和马鞭。
不要跑了!
拉住它!!
可这些呐喊却没能说出口,而是死死堵在喉咙里,堵得陆茫喉间刺痛,弥漫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就在这时,异变突生。
在最后的二百五十米,一直领先的追月的速度忽然肉眼可见地慢了下来,转瞬间掉到了最后。原本跟在它身后的马群很快便超越了它,它却无力再继续往前跑去,只是踉跄着,步履蹒跚地走到一旁,把背上的骑师不轻不重地甩了下来。
另一边,之前一直贴在追月身边的10号赛马爆发出了惊人的末脚,甩开了身后的一众赛马,硬生生拉开两个马身的距离,冲过了终点线。
陆茫整个人摔回座位上,觉得浑身的力气连带灵魂都在一瞬间被抽走。
维伯周围的观众有的在欢呼,有的在对这场意外感到担忧。他看着追月的骑手拉住缰绳试图安抚陷入痛苦的追月,练马师、马主,还有工作人员一拥而上,将它围了起来,只觉得视线难以聚焦。
“怎么回事?”
“受伤了?会不会有事?”
“好像站不起来了。”
耳边的所有声音如海浪般交叠在一起,失真,变成一阵嗡嗡的响声,直到一切归于平静。
心跳难以平复,令心脏像是快要炸开似的痛起来,呼吸也开始变得不稳,就连手指尖都忍不住颤抖起来。陆茫不敢把目光投向赛场,他抓起背包,有些狼狈地挤过身旁的观众往外走去。
他迫切地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却不知道去哪里。
过快的心跳让身体像是失控一样,冷汗不知不觉间浸透了整个后背,他连站都站不住了,扶着墙跪下,打开背包想把药翻出来,手却抖得不行,眼前也一阵阵地发黑。
药在瓶子里碰撞发出轻响,但陆茫还未来得及把药咽进嘴里,就感觉到最后一丝理智以可怕的速度被身体里积聚的恐慌彻底挤出来。
失去意识前,他在模糊到极点的目光之中,看到有人向他走来。
——咔哒。
药瓶脱手落在地上,沿着地面滚动。里面的药片跟着撒了出来。
正好目睹了一切的傅存远快步上前,伸手捞住了差点就要和地板来个亲密接触的陆茫。
他皱起眉头摘下这人的帽子和口罩,在看清楚脸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迅速把人打横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