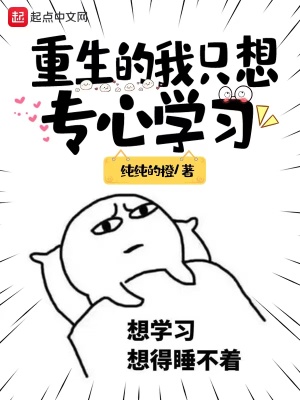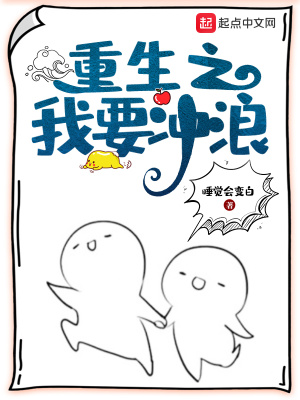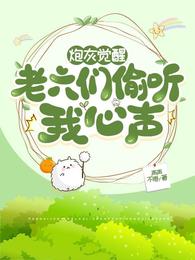中文小说网>穿越古代当农夫 > 第1235章 新任知府(第1页)
第1235章 新任知府(第1页)
江县令扶起他们,眉头拧成了疙瘩。
他何尝不知道邻县的难处,可丰水县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今年虽说收成不错,但除去上缴的赋税,再留足本县百姓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能匀出来的本就不多。
这几日来借粮的官员一波接一波,再这么借下去,丰水县自己都要见底了。
“诸位同僚,”江县令声音沙哑,“丰水的粮食,是百姓一滴汗一粒米攒出来的。
借,我能理解;但要多少,怎么借,得有个章程。”
他转身对身后的主簿道:“去,把粮仓的账册拿来,让诸位看看我们的底。”
账册很快抱了过来,上面一笔一笔记着入库、出库的粮食数量。
各县官员看着上面的数字,脸上的急切淡了些,却又添了几分为难。
——丰水县能匀出的粮食,分给十几个受灾县,实在是杯水车薪。
“江大人,”清河县丞红了眼,“哪怕先借我们够撑到开春的,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江县令沉默片刻,忽然道:“这样吧,每个县先按受灾人口借粮,每人每日半斤杂粮,先借一个月账目记清楚,来年秋收,你们按市价折算成银子还回来,或是用等量的粮食抵账。
——我丰水县可以不赚,但不能让百姓白辛苦。”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但有一条,借去的粮食,必须全部分给百姓,谁敢中饱私囊,我江县令第一个不饶!”
各县官员对视一眼,虽知粮食不多,却已是眼下最好的办法,纷纷拱手:“谢江大人!我们定当铭记这份情分!”
江县令摆摆手,让主簿带着他们去办理手续,自己则走到衙门口,望着外面依旧等候的差役和百姓,长长叹了口气。
他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想办法让受灾县熬过这个冬天,来年能顺利春耕才行。
风从街面吹过,带着一股淡淡的麦香——那是丰水县粮仓的味道,也是眼下多少人盼着的活命的味道。
江县令攥紧了手里的账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得让这些粮食,真正用到该用的地方去。
江县令刚把借粮的官员们送出大厅,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见一个衙役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手里的皂帽都歪了:
“大人!府城来的信使求见!就在外面候着!
“府城信使?”
江县令眉头一挑,心里咯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