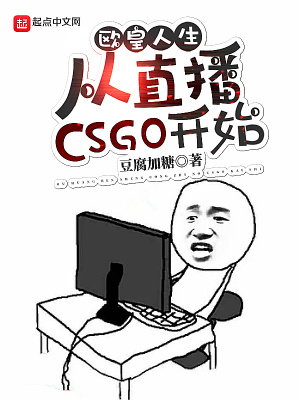中文小说网>北宋家生子txt > 第 4 章(第2页)
第 4 章(第2页)
他立即结巴起来。
季山楹淡淡道:“起来,家里今日出了大事,你一会儿再说。”
季荣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就站起身了。
他犹豫了片刻,竟然往后退了两步,站在了妹妹身边。
季山楹嫌弃:“蹲下来,你挡光了。”
“哦。”
季大杉阴晴不定看着这一对兄妹,没有开口,窄小的外间一时间落针可闻,只有许盼娘悲切哭声。
季山楹抬眸看向他,季大杉面无表情。
“祖父是先家主的大管家,曾经在侯府中呼风唤雨,一次外出舍身相救,以命得了先家主的记挂。”
家里的事情,许盼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季山楹早就烂熟于心。
她淡淡道:“阿爹十岁就没了父亲,十八岁没了母亲,即便有英勇护主的事迹,到底孤木难支,还是侯爷心慈,特地命人给你安排了这一桩亲事。而当年主家赏赐的珍物,也慢慢耗费殆尽,如今只剩下这一方澄泥砚。”
“是吧?”
澄泥砚是四大名砚之一,品相好的售价极为昂贵,尤其季家藏的这一方还是先代归宁侯所赐,是澄透漂亮的朱砂红色,是相当珍贵的。
季大杉把它当成是季家重复荣光的命根子,盼着如同父亲在世时风光无限,自然宝贝得紧,从来不肯展露人前,之前季福姐病得快死了,他也没拿出来。
女儿的命抵不过痴心妄想。
季山楹问过罗红绫,她估摸着这澄泥砚当出能有八十两左右。
不仅能偿还债务,还能给许盼娘换更好的药材,让她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对于季山楹来说,死物没有活人重要。
可季大杉不是她。
因此,听到季山楹的淡漠诘问,他几乎暴跳如雷。
“反了天了,反了天了,那是用你祖父的命换来的,怎么可以当了?”
“你当的还少吗?”季山楹冷声嘲讽。
季大杉被堵得满脸通红,眼睛里的血丝赤红一片。
季山楹冷冷看他:“你若不肯,就用你自己的命去填补。”
她非常坚定:“阿娘的药钱一文都不能动,需要靠着这药续命,我们全家也没有能力替你偿还债务,咱们都卖身给了侯府,可没办法再卖一次,那五十一两银子,你自己去想办法。”
“是卖肉卖血,还是把那方砚台当了,随你。”
别看季山楹年纪小,可说出来的话却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