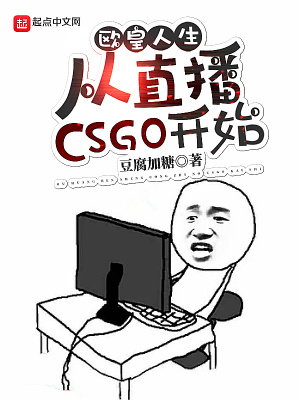中文小说网>那狼女又把师兄咬了最新章节更新内容 > 1212(第4页)
1212(第4页)
只有孕育在母体中的双生子才拥有这样的时刻。
……可是,双生子不会在长大后还玩嘴对嘴的游戏。
江玄肃恍惚地垂眼。
身下的被子拱起一团,阿柳看上去终于平静了。
旁人若是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只怕又要骂她是不通人伦的畜生。
此念一出,江玄肃背上竟浮起一层冷汗。
错了。
阿柳不是畜生。
不知者无罪,知道什么不能做还放任自流,才应该被骂畜生。
他才是……
太阳落山,屋子里越来越暗,翻倒的家具变换形状,整个世界仿佛也随之扭曲。
幻听似的,江玄肃耳边响起白玉峰顶夜晚呼啸的风声。
童年时,他曾一夜又一夜跪在阁楼上听它,从天黑听到天亮。
江玄肃用力地眨眼,再回神,眼前仍是旅店的厢房。
他松开被褥站起来,一步步朝后退,退到门口了,阿柳仍没有动。
她还蜷在被子里,看上去根本不想搭理他。
屋子里一片狼藉,正如他的心境。
江玄肃望着那团被子下隆起的身影,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有些话,她不愿听,他也不想告诉她,谁都有害怕被人知晓的秘密。
几百里外就是钟山,宗门里容不下异类。
他只是想让她变好。
他坚信,无论是什么样的恶习,她都能改。
……毕竟当年的他也都改了。
-
第二日,又是同样的跑马奔波,到了傍晚,转过最后一个山头,视野中陡然出现一片形状奇异的高山。
夜幕低垂,两侧峰头连绵如水浪,合到中间,却陡然出现一道更加浓黑的裂隙。
像有一把剑从中劈开群山,形成幽深的峡谷,马道一路延伸,通往那峡谷之中。
如果探头眺望,可以隐约看见峡谷入口处亮着灯火的阁楼。
邵忆文叱了一声,胯下马儿随之加速,跑到最前方。
她侧头看身后同乘一匹马的阿柳,指着远处的光亮讲解道:“前面就是设在钟山边缘的界碑,界碑旁有烛南宗的驿站,我们今晚在那里休息。”
阿柳不作声,也不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