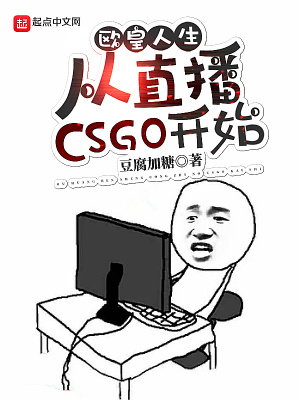中文小说网>那狼女又把师兄咬了最新章节更新内容 > 404(第5页)
404(第5页)
叫他,是为了提醒他拜入师门时立过的誓,提醒他身为君子什么是不应当做的。
江玄肃脊背一僵,缓缓坐下,闭了闭眼。
修士离开钟山后就不能动用灵息,丹田也随之滞涩停用,没了外界的力量帮助他恢复清明,只能靠他自己凝聚神识,压抑情绪。
梁继寒抱歉地对项姥姥笑笑:“少年人,性情难免浮躁,冲撞了您,还请多包涵。”
项姥姥没说话,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冷哼一声。
最烦和这些又修道又读书的人打交道,不肯痛痛快快发脾气,莫名其妙被惹急了又打不过他,平日还总自诩什么谦谦君子。
两个装货。
小装货道行浅,压不下脾气,老装货心计深,知道藏住心思,总之都不好惹。
江玄肃坐下后平复了呼吸,心绪却不能平,整理一番思路,看向项姥姥。
“方才隔壁的动静您都听见了,她下山才六年,与人交流已不成问题,还学会这么多方言,可见天资聪颖。山林间弱肉强食,她逞凶是为了自保,吃人是为了维生,毕竟没人教过她什么不能吃。下山后她随您四处卖艺,旁人都拿她当异类看,她遭人冷眼笑话,自然对外界抱有敌意。若能教她读书写字,授她礼仪规矩,耐心对待她,使她体会到为人的温情,让她开灵智、明事理,我不信她还会这般野蛮。”
江玄肃言辞恳切,梁继寒在旁边听得欣慰微笑,不时颔首,项姥姥却始终抱着胳膊冷眼相待。
殊不知她心里骂得更难听。
十几岁的年纪,x毛都没长齐,还敢来教老太婆做事。说这么多套话,无非是老装货拿着书本教他的,自己根本没亲身经历过,等挨那狼女咬上两口,看他还能不能这般振振有辞。
项姥姥把长鞭丢在桌上,朝门口一歪头:“随你怎么说。反正远水解不了近渴,不是验胎记吗?你不许我打她,那你去让她安分。”
恰在此时,隔壁传来邵忆文绝望的呼唤:“别脱!外衣捡起来穿上!”
江玄肃听在耳中,顿时愣怔,随即脸颊发热:“男女有别,她刚沐浴完,衣冠未整,我怎能……”
项姥姥翻白眼:“我们一帮粗人,没这么多讲究。你出门去附近问一圈,谁家老大没给家中弟妹把过尿擦过屎?年龄相仿的,一起穿开裆裤长大,也没少看过对方的光屁股。她又不是没穿衣服,你如果心里没有杂念,又怎会这般顾忌?刚才摆着哥哥的谱护短,我还道你是真心实意把她当妹子看,现在要你管教她,却突然怯场了。温情呢,耐心呢?你是怕被她咬吧?”
梁继寒侧头,见江玄肃耳根逐渐浮起薄红,心道这老妪说得太过火,刚要圆场,突然见他再次起身。
“我不怕。”
-
阿柳感觉脖子快要炸开了。
一群骗子。
说什么验胎记,验完以后请她吃顿好饭,结果一进县衙就被那个女人抓去洗澡,连饭盘的影子都没见着,现在洗完了,他们还打算把她关起来毒死。
那个小瓶里装的药水一倒在她脖子上,她就痛得厉害。
不光是皮肉痛,简直要钻到骨子里一路刺穿她全身。
从前在山上饿极了吃泥巴和石子之后也是这样痛,痛完以后手脚还会烧得慌,几年过去,她都快忘了那种感觉,没想到今天突然又被这药水勾起回忆。
她缩在角落里,冷冷瞪着门口的女人。
这几个人都比她强,一时半会打不过,哼,如果她再多吃几年饱饭,练几年功夫……